
作者简介:
九里安西王,本名王志榮,1985年留學美國,蒙大拿大學微生物碩士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電腦碩士。曾在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界打滾十年後,轉入電腦界,又在資料庫龍頭甲骨文公司打滾十年後,2011年轉入美國聯邦財政部任公務員,2025年初,被總統川普強迫退休。2013年開始寫作,文章常發表在臺灣的聯合報、中國時報、人間福報、中華日報、金門日報、文訊和美國世界日報等副刊和旅遊版。也以筆名王稚融兼任美國世界日報華府通訊記者,及華府新聞日報自由撰稿人,曾任華府作家恊會會長,現任華府書友會會長,著有「走過零下四十度」一書。

為了年輕十歲的抉擇 / 九里安西王
年輕時,我常為了頭髮太多而煩惱,如今年紀漸長,頭髮未見減少,又為了愈來愈多的白髮傷腦筋。
蘇東坡曾自嘆:「多情應笑我,早生華髮」,應是年少白頭。大學時,班上有位同學年紀輕輕便滿頭銀絲,予人一種穩重內斂之印象,曾令我暗自羨慕。
一位朋友的父親九十多高齡仍滿頭黑髮,而這位與我同齡的友人髮色依舊濃黑,看起來硬是小我十歲。髮色改變似與基因有關,然而歷史上著名的伍子胥過昭關,一夜白頭的故事,也道出白髮可能來自生活的壓力。
本世紀初,我在美國資料庫大廠甲骨文(Oracle)工作的那十個年頭,幾乎每天都為工作賣命。日夜奔波,經常到全美各地出差,解決客戶難題。面對客戶語出驚人的要求:「如果連你們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,全世界就沒人能解了!」更多的時候,要等所有人下班後,我們才開始「上班」工作,而且必須在隔日開工前修復系統,通宵達旦是家常便飯。
在甲骨文工作第五、六年之時,正值年方近半百,發現額頭悄悄冒出幾縷白髮。剛開始,還能一根根拔除,意圖與時光抗衡。但漸漸地,它們似野草般滋長,拔也拔不完,儘管我的頭髮非常濃密,仍不免擔心拔禿了頭。
記憶中,民國七十年代有一檔相當轟動的電視節目《武器大觀》,主持人黑幼龍風度翩翩,辯才無礙。然而,最令我難忘的,卻是他額頭上那一撮猶如雪落青松的白髮,讓人聯想到智慧與歷練。那一抹白,深植於我的記憶長河。巧合的是,我最初的一撮白髮,也長於右額頭,彷彿無聲地向黑幼龍致敬。
人們總認為高科技產業是年輕人的世界,在輝達的黃仁勳還沒有爆紅前,白髮蒼蒼的人往往令人質疑效率與創新力。相較之下,許多白人年過五旬已銀髮滿頭,卻不顯老,可能因膚色白皙反而更平添風采。由於我經常飛遍全美見客戶,週末也在大學和補習班兼課,總不想讓客戶和學生見我有「過氣」之貌,為了職場保護色,於是開始定期染髮。
2011年轉換新職後,成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務員,雖然仍是電腦部門最高階的企業建築師(Enterprise Architect),但不再需要面對客戶,染髮頻率也漸漸減少。
新冠疫情期間,改成在家遠端工作,乾脆不再染髮,任白髮從髮根鋪陳至髮尖,化為銀絲海洋。某次,在作家協會的線上演講中,一位台灣的朋友在銀幕前驚呼:「哇,安西王的頭髮怎麼全白了?」
由於白髮分布不均,前額白髮較多,我索性改變數十年如一日的西裝頭,改梳後掠式髮型,竟意外被不少朋友戲稱為「董事長」頭,髮型竟然也是人們對社會地位的想像。
妻子也曾打趣,原本說好的「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」,我卻不等她,一路狂老。這句玩笑話,讓我意識到,不僅時光在推我前行,連身邊人也會察覺歲月的痕跡。
一位昔日高富帥的同學,幾年前一場大病癒後,髮色轉成灰白,仍活力滿滿,經常健行爬山。同學會上提及,某日搭捷運,一位年輕人主動讓座,他連忙婉拒,旋即轉頭,站到另一邊。不料另一邊坐著一位老先生對他揮手:「你還是去坐吧!」他困惑問我們:「我真的看起來那麼老嗎?」眾人嘴說「不會啊!」心中卻皆默默點頭。

然而白髪在日常生活中並非沒有好處。在公車或捷運上,年輕人會自動讓座,在美國有許多餐廳、連鎖店和大眾運輸系統都會提供老人特價,沒有人會再質疑,因為白髪就是證件。
如今染髮的時機,僅剩返台探親或遠行前。為給久未謀面的親友好印象,染上一頭烏黑的頭髮,不只讓人年輕十歲,似乎亦能讓重逢少幾分感傷。
2023年10月,疫情後首度返台。行前沒空染髮,儘管歷經廿四小時長途飛行,清晨抵達台灣,非常疲憊,第一件事竟非休憩,而是尋覓理髮店修理門面。在新莊岳母家附近的傳統市場逛了一圈未果,忽見一位髮型整齊的大叔,問其剪髮處,他指著前方巷口:「就在前面轉角的巷子裡,有一間迷你理髮店,已經開門了。」
那是一家未被谷歌地圖標示的家庭理髮店,僅有兩張椅子,店主是位和藹的老阿嬤。我問:「是否可以理髪順便染髮?」她抬眼估量道:「剪加染,五百五。」
她乾淨俐落地先幫我頭髮剪短、打薄後,開始上染劑。但才染到一半,便聽她嘀咕著:「你頭髮還是這麼多,又這麼白,這樣成本不夠,能否再加五十?」自小到大早已習慣,我常被理髮師抱怨頭髮太多,何況已染了半邊,只得應允。
上好染劑後,她將我的椅子放平,讓我幾乎躺著,自己跑去門口與鄰居閒聊,我便在染劑氤氳中小睡了一覺。醒來後照鏡子,頭髮果然黑得發亮。
翌日同學會,老同學笑問:「你是不是在美國修仙,怎麼看來比我們年輕十歲?」
雖然白髮如雪是另一種風華,如詩云「白髮漁樵江渚上,慣看秋月春風」,更是走過風霜的見證。若能帶著從容與幽默面對自己的外貌,不論染髮與否,終究是個抉擇。但是我問自己:「下次返台,我還會染髮嗎?」
「會的」,誰不想在舊友眼前,年輕十歲呢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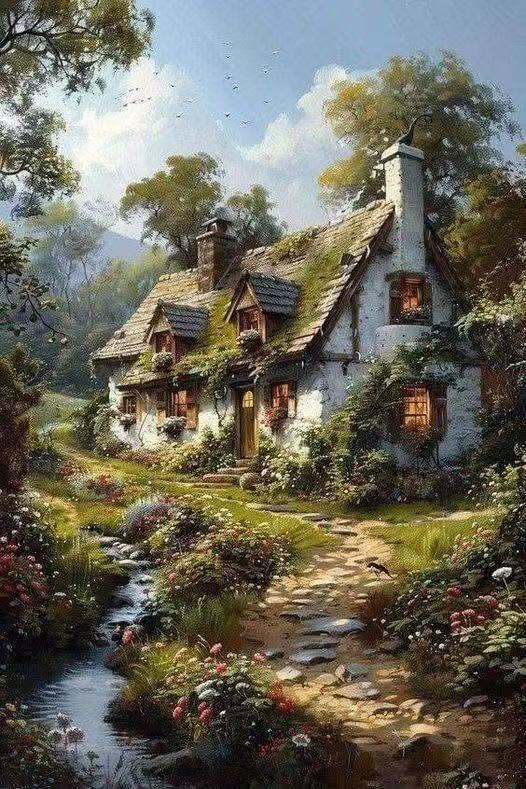
從〈一分錢的祝福〉談我的寫作之「路」
我的筆名「九里安西王」,是2015年10月25日和華府三位作家到紐約拜訪王鼎鈞後「改名」的結果。當時我在《華府新聞日報》投稿,用的是英文名字 Julian。王鼎鈞笑說:「寫中文怎麼用英文筆名?」回家後我將自己英文名字的音譯,Julian C. Wang,翻成「久」里安西王,還得意地告訴太太。她卻說:「不好,聽起來像日本人名字!」於是我把「久」換成數字「九」,成為「九里安西王」,既有「九五之尊」的味道,也算自己「封王」。
至於我的寫作之路,始於2011年離開甲骨文公司,進入美國聯邦政府工作後,開始走起。因為工作壓力從「地獄」瞬間轉到「天堂」,生活節奏放緩,讓我有時間提筆。2013年,開始在《聯合報》部落格寫文;2015年投《華府新聞日報》;2016年起向《世界日報》投稿。
韓秀說寫作要「坐得住」,我覺得還要「走得動」。有次在隱地編的散文集裡,讀到作家季季說文章是「走出來的」,深有同感。
說我的寫作之路是「走」出來的,一點不假。2005年,我領養了一隻漂亮的喜樂蒂牧羊犬「弟弟」。為了帶牠運動,也為了健身,我每天逼自己走一萬兩千步。2015年弟弟離世後,步數慢慢減到一萬,如今雖定在八千步,但實際常走到一萬。
走路時,每每發現靈感不斷,我就用手機隨時記下,靈感可能是一個詞、一段話,甚至一張照片。如今手機備忘錄裡有兩三千條待完成的靈感,有的完成兩成,有的五成,有的七、八成,每隔一段時間,我就挑出完成度高的,或是有幾段相關的靈感,從手機寄到電腦上繼續修改,直到可以投稿。如果在修稿的途中遇到瓶頸,我也會站起來快走,讓大腦僵化的思緒可以變得流動。
〈一分錢的祝福〉就是這樣誕生的。故事源於去年到西雅圖和阿拉斯加郵輪旅行,先是在西雅圖民宿門口,後來在郵輪房間門口,各看到一分錢,想到小費文化,便記下來。為了湊足篇幅,我還寫進了一分錢上的林肯頭像,與在春田市與華府福特劇院看到的林肯銅像,共同組成這篇文章,刊登於6月7日刊登在《世界日報》副刊。
旅遊對我來說,也是「行萬里路」的另一種寫作。早期寫部落格時,我常一個城市、一個城市記錄下來,像日記,少了變化。後來我學會用旅行來襯托主題。例如西班牙之行,我寫了九篇不同主題的旅遊文章,分別刊在《聯合報》繽紛版、《世界周刊》和《人間福報》旅遊版,形式上都是散文。
正如王鼎鈞所說:「寫作是朝思暮想,千回百轉,才下眉頭,又上心頭。」像極了當年交女朋友時的心態。今年五月被總統川普強迫退休之後,更是每天寫個不停,今年至今已經有12篇文章登上台灣的聯合、中時、人間福報、美國世界日報等副刊和三家雜誌,另外還有四篇尚未刊登。
由於理工的背景,讓我的文章漸漸有了固定風格,結合人文、歷史與生態知識,兼顧理性與感性,保持輕快、好讀、幽默與溫馨,並儘量與台灣或中華文化產生連結。走路、觀察、記錄,再慢慢打磨,便成了我的「寫作之路」。

《美洲文化之声》简介:
《美洲文化之声》国际传媒网(Sound of USA)成立于2016年,是美国政府批准的综合网络平台,主要从事华语文学作品的交流推广。目前已与Google、百度、Youku、Youtube 等搜索引擎联网,凡在这里发表的作品均可同时在以上网站搜索阅读。
我们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,同时提倡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唯美主义风格,为世界各地的华语文学作品交流尽一份微博之力。同时,美洲文化之声俱乐部也正式成立,俱乐部团结了众多的海内外知名诗人、作家和评论家,正在形成华语世界高端文学沙龙。不分国籍和地区、不分流派,相互交流学习,共同为华语文学的发展效力。
传播中华优秀文化、倾听世界美好声音,是我们美好的追求和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总顾问:森道.哈达(蒙古国)
顾问:蓬丹(美国)、李发模(中国)、段金平(美国)、祁人(中国)谭五昌(中国)、张素久(美国)、林德宪(美国)、萨仁图雅(中国)、周占林(中国)北塔(中国)
总编辑:韩舸友(美国)
副总编辑:冷观(美国)、jinwenhan(加拿大)
Artificial Intelligence,创作艺术总监:张琼(美国)
国际交流中心总监:芳闻(中国)
中国交流中心总监:夏花(中国)
编委:寒山(韩舸友/美国)、冷观(美国)、jinwenhan(加拿大)、刘乃歌(美国)、伊萌(美国)、张琼(美国)、芳闻(中国)、夏花(中国)范群(中国)、紫晨(美国)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